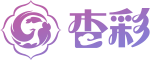不要浪费一场好泡沫
日期:2025-10-29 14:53:54 / 人气:53
"可能,是时候重新理解泡沫。
在某种意义上讲,“泡沫”并非只是单纯的市场狂热或金钱游戏,它更是一种“以信念加速未来到来”的文化现象,是一场拥抱未来的信任实验。
最近看到两份资料,一本新书《Boom: Bubbles and the End of Stagnation》 (《繁荣:泡沫与停滞的终结》),一份《金钱的艺术》作者摩根·豪泽尔合作基金的投资复盘,都视角清奇,试着把它们结合在一起,探讨一下新时代的泡沫和风险取向。
一、普通人可能“不够泡沫”
在多数大众认知里,“泡沫”往往与荷兰郁金香狂热、房产投机或庞氏骗局画上等号,既荒诞又危险。
但是,美国科技投资公司 Anomaly 的两位合伙人拜恩·霍巴特和托比亚斯·胡伯在他们的新书 《Boom: Bubbles and the End of Stagnation》 (《繁荣:泡沫与停滞的终结》,以下简称为繁荣)中,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:这些“近乎疯狂”的昙花一现,实际上可能正是人类社会最需要的“试验场”。
在他们看来,一些历史上推动人类技术大跨步的关键节点(例如美国曼哈顿计划、对互联网与半导体的早期狂热等),无一不是某种形式的“泡沫”驱动出来的。
两位作者将“泡沫”视作一群志同道合者的“深度合作”: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掌握了某个尚未被大众认可的真理,因而抱团聚集,朝着那个充满想象力的目标孤注一掷。
即便外界质疑,他们也能通过内部的“认知封闭”式自信迅速达成协作、投入大量资源,加速把未来拉近到眼前。一旦目标实现,他们便可彻底重塑行业格局;即便失败,他们也往往为下一轮创新留下了经验或技术积累。
之所以说我们普通人“不够泡沫”,是因为人类对于风险和失败的恐惧,使得许多人宁可选择将大量资金投向稳健的指数基金或低波动资产,而不愿进入高风险、高不确定性的领域。
霍巴特与胡伯认为,正是这种对冒险的畏缩,扼杀了不少“可能颠覆未来”的机会。他们呼吁,需要有人甘冒风险去推动“伟大事业”,因为哪怕只有极少数成功,一次成功就足以改变世界。
二、泡沫不是那么简单就产生的
“泡沫”带来的最大驱动力,在于形成一股极短期内的“资源汇聚”。
可以想象,一家早期创业公司,如果只是孤军奋战,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招揽足够的专家、资金和社会关注度;但当一股“跟风热潮”出现,资本和人才便可能蜂拥而至,一些看似疯狂的产品就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得到验证或失败。
这种“速成式”繁荣常常以泡沫破裂告终——市面上最常见的例子也多是此类。但在霍巴特和胡伯眼中,这些破裂也未必都是坏事。因为“崩盘”意味着过去的假设证明不可行,催生行业冷静反思,为下一步的真正突破扫清障碍。
摩尔定律的启示
曾任仙童半导体和英特尔联合创始人的戈登·摩尔(Gordon Moore),在 1965 年发现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每隔一年半就翻一倍。最初,这只是基于对现象的归纳,但业内却把它升格为“定律”,并且各方愿意信守——芯片制造商敢于大举研发更高性能的芯片,而软件开发商也提前布局需要更多硬件算力的新应用。
在这种“你做硬件,我做软件;你越做越好,我就用得越多” 的互相拉动中,半导体行业才得以呈爆炸式成长。可以说,这就是一次“泡沫式乐观”与集体协作的成功案例。
为什么现在缺乏这种“快速合力”?
当我们回顾 2020 年全球新冠疫情时,不少人认为,整个世界其实急需一次“医疗与防疫技术的泡沫”——快速检测试剂、可自检多病毒的家用套件、空气过滤系统乃至疫苗产能扩张,若能像半导体行业对待摩尔定律那样大规模投入、深度协同,也许就不会出现之后的种种被动。
然而现实往往是,企业在真正扩产后,却无法得到订单支撑,甚至政府部门的审批与资源调度也没能进入“泡沫模式”。结果是失去一次大力升级公共卫生防控能力的契机。
这说明,“泡沫”并非只关乎商业投机或初创企业的投融资,而是一种协同机制。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“集体狂热”,资源便难以在短时间内集中,创新也便会一再延缓。
三、风险投资的“既要又要”
风险投资行业似乎天生与“泡沫”紧密相连:许多初创企业的崛起恰恰需要外部资金大举涌入,帮它们快速验证技术和商业模式。但也正因为风险过高,许多VC倾向于“分散投资”,也就是以较小的单笔资金押注多个项目,以期在其中捕捉到某个“超级赢家”。
然而,如同霍巴特和胡伯所说,那些真正改变世界的突破,常常需要来自外部和内部的“双重信仰”。一方面,创业者得自我催眠般地投入;另一方面,投资人也要拿出具备足够分量的资本,才能“把不可能变成现实”。
怎样的资金配置才最适合推动这一过程?这是VC领域永恒的难题。
分散还是集中
从传统角度看,分散投资可以降低风险,因为无论哪个项目失败都不至于让基金全军覆没;而集中投资,即“少数大额下注”,一旦踩中超高回报的爆款项目,回报率就会令人惊叹。
对于不同的基金规模、不同阶段的企业来说,这个抉择也不一样。早期天使投资往往单笔较小、数量偏多,因为信息不透明、失败率高;成长阶段投资则有更多投后跟进和尽调机会,可以考虑加大单笔下注,或者跟投某个表现极佳的项目。这些操作细节都需要基金管理者有灵活的策略。
风险与收益的幂律分布
风险投资中有一句流行的观点:“VC 回报遵循幂律分布”——极少数投资往往贡献了绝大部分的基金收益。也因此,找到那家潜在的超级黑马,往往比多投几家中规中矩的公司更能带来指数级回报。
在理想情况下,如果投资人有强烈的信念(conviction)认为某家公司具备成为“独角兽”或“十角兽”的潜质,那么集中砸下重金,也就更有可能收获超预期的回报。
四、风险投资组合的数学与局限
在尝试将风险投资这门“艺术”转变为“科学”时,人们提出了许多数学工具来辅助决策,包括凯利准则、幂律模型和蒙特卡洛模拟等。它们确实能提供一定指导,但也存在各自的局限。
凯利准则(Kelly Criterion)
核心思想:凯利准则能帮赌徒确定在每一次赌博中“最大化长期收益”的最佳下注比例。引入投资场景后,它似乎能告诉我们,给每个创业公司应在基金中分配多少资金。
局限性:
•它假设我们知道“成功的概率”和“回报率”,但实际中这些数据往往扑朔迷离;
•它还假设可以连续复利投入,但VC基金通常被锁定 7~10 年,无法随时调整。
幂律概率方法
基本思路:给一个“可能带来 20 倍回报的公司”设定 5% 的成功机会,假设不想错过这种公司就必须投资足够多的标的,否则错过概率会随着投资标的数目不足而直线上升。以此来推导需要投资多少家公司。
局限性:
•把退出结果简化成“要么爆发要么归零”过度理想化,忽略中间那些表现平平但可能会产生一定收益的项目;
•设定的失败阈值往往相当主观。
蒙特卡洛模拟(Monte Carlo Simulation)
核心方法:基于成功率、退出倍数等假设,运行大量随机场景模拟不同配置下的收益分布。
局限性:
•模拟结果依赖输入假设;如果输入的数据或参数有偏差,最终也会产生极大误差;
•历史回报并不能完全代表未来,比如只要加入对 Facebook、Uber、Google 等超级投资案例的数据,均值就会被极端拉高到一个看似“可怕”的数字。
这些方法的启示是:数学能帮助我们获取一些大方向上的指引,但无法绝对告诉你何时要 all in,或者何时要见好就收。 具体投资决策还取决于当下的市场环境、团队信任、条款谈判以及个人或机构的战略考虑。
五、一笔把500万美元变成1亿美元的大胆赌注
谈到高信念投资,最近看到一个经典案例:摩根豪泽尔的Collaborative Fund 在 2015 年拥有一支 2500 万美元的基金,却做出了一个在行业内看来“异常大胆”的决定:
把其中 20%(也就是 500 万美元)一口气投给了一家初创公司。几乎没人预料到,这家公司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,就为基金带来了超过 1 亿美元的回报,相当于把基金本身的价值翻了四倍。
它是怎么做到的?
幂律结果: 并不是每一次大赌注都会成功,但风险投资回报分布本来就极具极端性:那支基金成功捕捉到了“极少数的爆发性机会”。
信念驱动: Collaborative Fund 当时非常看好该团队的综合素质和市场走向,认定它有潜力成就一番大业。正如书中所提到的,“泡沫”的一大特征是相信“未来被提前拉近”。有了这种强烈信念,才敢下重金。
专注度与资源投入: 较大的持股比例意味着你在公司董事会、战略制定和人才招聘中更有话语权,可以倾注更多资源,与创始团队深度绑定。这样一来,你也更容易做出精准的后续投资决策。
失败了又会怎样?
专注式投资的痛处: 万一公司最终走向失败,那么占了基金 20% 的押注可能直接拖垮整个基金,伤害到 VC 机构的声誉和未来募资能力。
应对策略: 在极度信念的基础上,依然要有完善的尽调机制与风控措施,对企业发展节点进行评估和跟踪。 Collaborative Fund 之所以敢做这个决定,显然已对项目前景、团队执行力和市场需求做了深入调研,也留出必要的后续跟投或止损预案。
对比常见的“广撒网”模式,高信念、大额下注的做法在风投圈并不多见,却往往在幂律分布中诞生出耀眼的收益。而在霍巴特和胡伯的语境里,这种做法也正是对“泡沫思维”的某种实践:你要有足够的“疯劲”去相信这个目标,并愿意为之投入超越常规的资源。
六、让“泡沫”与理性投资并存
回顾这两条看似不相干的线索——一个是关于“泡沫”的热情洋溢与协同创新,另一个是风险投资领域对集中押注与分散策略的讨论——我们不难发现,它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核心:“高风险、高回报的极端下注究竟值不值得?如何在其中平衡理性、信念与协同?”
霍巴特和胡伯在 《繁荣》 中期待更多人能“甘愿受骗”,即愿意投入到某个“明知风险巨大但可能带来惊喜”的冒险过程。
这种呼吁并非鼓励盲目吹牛或金融欺诈,而是呼吁更多人能突破对失败的恐惧、对未知的排斥,去创造那些只有“集体信念”才能完成的巨大工程与技术革命。
就像戈登·摩尔发现的那道“晶体管翻倍曲线”,正是这股“看似疯狂”的信任与协同,才把预言变成了自我实现的产业定律。
另一方面,豪泽尔基金所表达的风投观点则提醒我们,无论怎样的狂热都得有一定的专业度与科学性辅助。
凯利准则、幂律模型、蒙特卡洛模拟等方法虽然各有不足,但至少告诉我们,“赌注”应当建立在相对理性的评估基础上;在选择专注投资还是分散投资时,也要考虑到基金的规模、LP(有限合伙人)的容忍度以及团队自身的投资能力。过度冒险会危及生存,而过度保守则往往错过真正的超级机会。
综上所述,在这个竞争愈演愈烈、技术更迭越发迅速的时代,“泡沫式”的快速汇聚与冒险可能依然是催生重大突破的关键机制。正如 Collaborative Fund 的那笔 500 万美元大额下注所显示——当你足够看好一个项目,并有能力沉下心来为之护航,便能在幂律世界中收获惊喜。
更重要的是,我们也不能将一切都寄托在数学模型或宏大叙事上;大胆的行动需要真切的信念,也需要在关键时刻拉下理性的刹车,把盲目的激进与严谨的判断相结合,方能把一次“泡沫”锻造成真正的创新浪潮。
也许,下一次影响全球的重大进展,就会诞生于一场我们尚不知晓的“泡沫”中:一群人认定了一种尚未被普遍认可的未来,并彼此深信不疑。有人拿出了超越常规的资金,有人拿出了全部的时间与才华。
他们放弃了对外界的无休止解释,把注意力全部投向了自己所坚信的那个终局。在外人看来自负又愚蠢,但在他们内部,这就是用双手把“可能”变成“现实”的过程。
从这个意义上讲,“泡沫”并非只是单纯的市场狂热或金钱游戏,它更是一种“以信念加速未来到来”的文化现象。风险投资人或其他资金方,则在其中扮演类似催化剂的角色:当理性的可行性研究与非理性的热情交融到位,彼此激发,或许就能迸发出影响几代人的强大动力。
当然,这个过程随时可能失控,甚至酿成巨大失败,但回顾人类的技术史,许多里程碑往往正是从一次又一次的冒险与挫败中淬炼出来。
正如霍巴特和胡伯所说:真正值得追逐的“泡沫”,从来就不是简单的金钱游戏,而是一场拥抱未来的信任实验。
"
在某种意义上讲,“泡沫”并非只是单纯的市场狂热或金钱游戏,它更是一种“以信念加速未来到来”的文化现象,是一场拥抱未来的信任实验。
最近看到两份资料,一本新书《Boom: Bubbles and the End of Stagnation》 (《繁荣:泡沫与停滞的终结》),一份《金钱的艺术》作者摩根·豪泽尔合作基金的投资复盘,都视角清奇,试着把它们结合在一起,探讨一下新时代的泡沫和风险取向。

一、普通人可能“不够泡沫”
在多数大众认知里,“泡沫”往往与荷兰郁金香狂热、房产投机或庞氏骗局画上等号,既荒诞又危险。
但是,美国科技投资公司 Anomaly 的两位合伙人拜恩·霍巴特和托比亚斯·胡伯在他们的新书 《Boom: Bubbles and the End of Stagnation》 (《繁荣:泡沫与停滞的终结》,以下简称为繁荣)中,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:这些“近乎疯狂”的昙花一现,实际上可能正是人类社会最需要的“试验场”。
在他们看来,一些历史上推动人类技术大跨步的关键节点(例如美国曼哈顿计划、对互联网与半导体的早期狂热等),无一不是某种形式的“泡沫”驱动出来的。
两位作者将“泡沫”视作一群志同道合者的“深度合作”: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掌握了某个尚未被大众认可的真理,因而抱团聚集,朝着那个充满想象力的目标孤注一掷。
即便外界质疑,他们也能通过内部的“认知封闭”式自信迅速达成协作、投入大量资源,加速把未来拉近到眼前。一旦目标实现,他们便可彻底重塑行业格局;即便失败,他们也往往为下一轮创新留下了经验或技术积累。
之所以说我们普通人“不够泡沫”,是因为人类对于风险和失败的恐惧,使得许多人宁可选择将大量资金投向稳健的指数基金或低波动资产,而不愿进入高风险、高不确定性的领域。
霍巴特与胡伯认为,正是这种对冒险的畏缩,扼杀了不少“可能颠覆未来”的机会。他们呼吁,需要有人甘冒风险去推动“伟大事业”,因为哪怕只有极少数成功,一次成功就足以改变世界。
二、泡沫不是那么简单就产生的
“泡沫”带来的最大驱动力,在于形成一股极短期内的“资源汇聚”。
可以想象,一家早期创业公司,如果只是孤军奋战,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招揽足够的专家、资金和社会关注度;但当一股“跟风热潮”出现,资本和人才便可能蜂拥而至,一些看似疯狂的产品就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得到验证或失败。
这种“速成式”繁荣常常以泡沫破裂告终——市面上最常见的例子也多是此类。但在霍巴特和胡伯眼中,这些破裂也未必都是坏事。因为“崩盘”意味着过去的假设证明不可行,催生行业冷静反思,为下一步的真正突破扫清障碍。
摩尔定律的启示
曾任仙童半导体和英特尔联合创始人的戈登·摩尔(Gordon Moore),在 1965 年发现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每隔一年半就翻一倍。最初,这只是基于对现象的归纳,但业内却把它升格为“定律”,并且各方愿意信守——芯片制造商敢于大举研发更高性能的芯片,而软件开发商也提前布局需要更多硬件算力的新应用。
在这种“你做硬件,我做软件;你越做越好,我就用得越多” 的互相拉动中,半导体行业才得以呈爆炸式成长。可以说,这就是一次“泡沫式乐观”与集体协作的成功案例。
为什么现在缺乏这种“快速合力”?
当我们回顾 2020 年全球新冠疫情时,不少人认为,整个世界其实急需一次“医疗与防疫技术的泡沫”——快速检测试剂、可自检多病毒的家用套件、空气过滤系统乃至疫苗产能扩张,若能像半导体行业对待摩尔定律那样大规模投入、深度协同,也许就不会出现之后的种种被动。
然而现实往往是,企业在真正扩产后,却无法得到订单支撑,甚至政府部门的审批与资源调度也没能进入“泡沫模式”。结果是失去一次大力升级公共卫生防控能力的契机。
这说明,“泡沫”并非只关乎商业投机或初创企业的投融资,而是一种协同机制。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“集体狂热”,资源便难以在短时间内集中,创新也便会一再延缓。
三、风险投资的“既要又要”
风险投资行业似乎天生与“泡沫”紧密相连:许多初创企业的崛起恰恰需要外部资金大举涌入,帮它们快速验证技术和商业模式。但也正因为风险过高,许多VC倾向于“分散投资”,也就是以较小的单笔资金押注多个项目,以期在其中捕捉到某个“超级赢家”。
然而,如同霍巴特和胡伯所说,那些真正改变世界的突破,常常需要来自外部和内部的“双重信仰”。一方面,创业者得自我催眠般地投入;另一方面,投资人也要拿出具备足够分量的资本,才能“把不可能变成现实”。
怎样的资金配置才最适合推动这一过程?这是VC领域永恒的难题。
分散还是集中
从传统角度看,分散投资可以降低风险,因为无论哪个项目失败都不至于让基金全军覆没;而集中投资,即“少数大额下注”,一旦踩中超高回报的爆款项目,回报率就会令人惊叹。
对于不同的基金规模、不同阶段的企业来说,这个抉择也不一样。早期天使投资往往单笔较小、数量偏多,因为信息不透明、失败率高;成长阶段投资则有更多投后跟进和尽调机会,可以考虑加大单笔下注,或者跟投某个表现极佳的项目。这些操作细节都需要基金管理者有灵活的策略。
风险与收益的幂律分布
风险投资中有一句流行的观点:“VC 回报遵循幂律分布”——极少数投资往往贡献了绝大部分的基金收益。也因此,找到那家潜在的超级黑马,往往比多投几家中规中矩的公司更能带来指数级回报。
在理想情况下,如果投资人有强烈的信念(conviction)认为某家公司具备成为“独角兽”或“十角兽”的潜质,那么集中砸下重金,也就更有可能收获超预期的回报。
四、风险投资组合的数学与局限
在尝试将风险投资这门“艺术”转变为“科学”时,人们提出了许多数学工具来辅助决策,包括凯利准则、幂律模型和蒙特卡洛模拟等。它们确实能提供一定指导,但也存在各自的局限。
凯利准则(Kelly Criterion)
核心思想:凯利准则能帮赌徒确定在每一次赌博中“最大化长期收益”的最佳下注比例。引入投资场景后,它似乎能告诉我们,给每个创业公司应在基金中分配多少资金。
局限性:
•它假设我们知道“成功的概率”和“回报率”,但实际中这些数据往往扑朔迷离;
•它还假设可以连续复利投入,但VC基金通常被锁定 7~10 年,无法随时调整。
幂律概率方法
基本思路:给一个“可能带来 20 倍回报的公司”设定 5% 的成功机会,假设不想错过这种公司就必须投资足够多的标的,否则错过概率会随着投资标的数目不足而直线上升。以此来推导需要投资多少家公司。
局限性:
•把退出结果简化成“要么爆发要么归零”过度理想化,忽略中间那些表现平平但可能会产生一定收益的项目;
•设定的失败阈值往往相当主观。
蒙特卡洛模拟(Monte Carlo Simulation)
核心方法:基于成功率、退出倍数等假设,运行大量随机场景模拟不同配置下的收益分布。
局限性:
•模拟结果依赖输入假设;如果输入的数据或参数有偏差,最终也会产生极大误差;
•历史回报并不能完全代表未来,比如只要加入对 Facebook、Uber、Google 等超级投资案例的数据,均值就会被极端拉高到一个看似“可怕”的数字。
这些方法的启示是:数学能帮助我们获取一些大方向上的指引,但无法绝对告诉你何时要 all in,或者何时要见好就收。 具体投资决策还取决于当下的市场环境、团队信任、条款谈判以及个人或机构的战略考虑。
五、一笔把500万美元变成1亿美元的大胆赌注
谈到高信念投资,最近看到一个经典案例:摩根豪泽尔的Collaborative Fund 在 2015 年拥有一支 2500 万美元的基金,却做出了一个在行业内看来“异常大胆”的决定:
把其中 20%(也就是 500 万美元)一口气投给了一家初创公司。几乎没人预料到,这家公司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,就为基金带来了超过 1 亿美元的回报,相当于把基金本身的价值翻了四倍。
它是怎么做到的?
幂律结果: 并不是每一次大赌注都会成功,但风险投资回报分布本来就极具极端性:那支基金成功捕捉到了“极少数的爆发性机会”。
信念驱动: Collaborative Fund 当时非常看好该团队的综合素质和市场走向,认定它有潜力成就一番大业。正如书中所提到的,“泡沫”的一大特征是相信“未来被提前拉近”。有了这种强烈信念,才敢下重金。
专注度与资源投入: 较大的持股比例意味着你在公司董事会、战略制定和人才招聘中更有话语权,可以倾注更多资源,与创始团队深度绑定。这样一来,你也更容易做出精准的后续投资决策。
失败了又会怎样?
专注式投资的痛处: 万一公司最终走向失败,那么占了基金 20% 的押注可能直接拖垮整个基金,伤害到 VC 机构的声誉和未来募资能力。
应对策略: 在极度信念的基础上,依然要有完善的尽调机制与风控措施,对企业发展节点进行评估和跟踪。 Collaborative Fund 之所以敢做这个决定,显然已对项目前景、团队执行力和市场需求做了深入调研,也留出必要的后续跟投或止损预案。
对比常见的“广撒网”模式,高信念、大额下注的做法在风投圈并不多见,却往往在幂律分布中诞生出耀眼的收益。而在霍巴特和胡伯的语境里,这种做法也正是对“泡沫思维”的某种实践:你要有足够的“疯劲”去相信这个目标,并愿意为之投入超越常规的资源。
六、让“泡沫”与理性投资并存
回顾这两条看似不相干的线索——一个是关于“泡沫”的热情洋溢与协同创新,另一个是风险投资领域对集中押注与分散策略的讨论——我们不难发现,它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核心:“高风险、高回报的极端下注究竟值不值得?如何在其中平衡理性、信念与协同?”
霍巴特和胡伯在 《繁荣》 中期待更多人能“甘愿受骗”,即愿意投入到某个“明知风险巨大但可能带来惊喜”的冒险过程。
这种呼吁并非鼓励盲目吹牛或金融欺诈,而是呼吁更多人能突破对失败的恐惧、对未知的排斥,去创造那些只有“集体信念”才能完成的巨大工程与技术革命。
就像戈登·摩尔发现的那道“晶体管翻倍曲线”,正是这股“看似疯狂”的信任与协同,才把预言变成了自我实现的产业定律。
另一方面,豪泽尔基金所表达的风投观点则提醒我们,无论怎样的狂热都得有一定的专业度与科学性辅助。
凯利准则、幂律模型、蒙特卡洛模拟等方法虽然各有不足,但至少告诉我们,“赌注”应当建立在相对理性的评估基础上;在选择专注投资还是分散投资时,也要考虑到基金的规模、LP(有限合伙人)的容忍度以及团队自身的投资能力。过度冒险会危及生存,而过度保守则往往错过真正的超级机会。
综上所述,在这个竞争愈演愈烈、技术更迭越发迅速的时代,“泡沫式”的快速汇聚与冒险可能依然是催生重大突破的关键机制。正如 Collaborative Fund 的那笔 500 万美元大额下注所显示——当你足够看好一个项目,并有能力沉下心来为之护航,便能在幂律世界中收获惊喜。
更重要的是,我们也不能将一切都寄托在数学模型或宏大叙事上;大胆的行动需要真切的信念,也需要在关键时刻拉下理性的刹车,把盲目的激进与严谨的判断相结合,方能把一次“泡沫”锻造成真正的创新浪潮。
也许,下一次影响全球的重大进展,就会诞生于一场我们尚不知晓的“泡沫”中:一群人认定了一种尚未被普遍认可的未来,并彼此深信不疑。有人拿出了超越常规的资金,有人拿出了全部的时间与才华。
他们放弃了对外界的无休止解释,把注意力全部投向了自己所坚信的那个终局。在外人看来自负又愚蠢,但在他们内部,这就是用双手把“可能”变成“现实”的过程。
从这个意义上讲,“泡沫”并非只是单纯的市场狂热或金钱游戏,它更是一种“以信念加速未来到来”的文化现象。风险投资人或其他资金方,则在其中扮演类似催化剂的角色:当理性的可行性研究与非理性的热情交融到位,彼此激发,或许就能迸发出影响几代人的强大动力。
当然,这个过程随时可能失控,甚至酿成巨大失败,但回顾人类的技术史,许多里程碑往往正是从一次又一次的冒险与挫败中淬炼出来。
正如霍巴特和胡伯所说:真正值得追逐的“泡沫”,从来就不是简单的金钱游戏,而是一场拥抱未来的信任实验。
"
作者:杏彩娱乐
新闻资讯 News
- 李湘账号被封禁风波持续发酵,王...01-27
- 全民救援!李亚鹏口碑大逆转:从...01-27
- 《镖人》曝“武侠本色”特辑:袁...01-27
- BLACKPINK要解散了?巡演...01-27